 |
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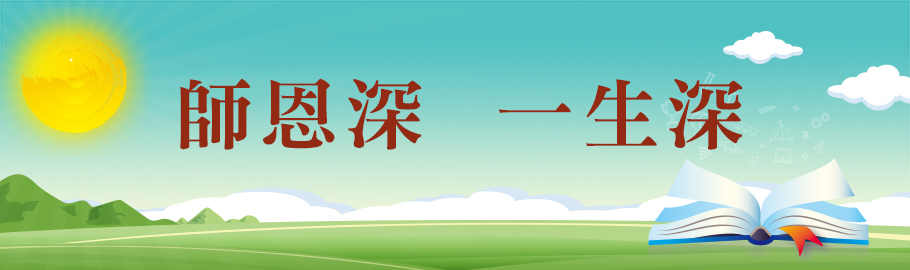
|
|
蔡幸君 那年夏天,小光是國一轉學生,健康的膚色襯映著單純的眼神,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,因學業及適應問題,他成為受輔學生。 小光的父親是日本人,媽媽是臺灣人,在日本出生的小光本由外婆照顧,父母離異之後,外婆帶著他回到臺灣,直到他小學時才回到日本,在加入學校棒球隊亦漸漸能融入之際,卻因媽媽工作的變動而被送回臺灣就讀國中,一來一往的學習與生活環境適應,小光錯過了學習中文的基礎。 輔導教師不會日文,小光中文也不太行,由外婆一手帶大的他,最溜的是臺語,在建立友善的輔導關係後,他長久壓抑的心情有了被理解的出口,小光漸漸釋放了心中的不安與悲傷,他曾說:「我在日本,同學說我是臺灣人;我在臺灣,同學說我是日本人,在他們眼中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臺灣人,那麼我究竟是誰?」小光在尋找他的認同,這是青少年階段很重要的事,而他卻如此沒有安全感與歸屬感。 小光總期待能回到日本和媽媽在一起,媽媽會打國際電話與輔導老師聯繫,在關心小光之餘,也表明小光在國中畢業前只能留在臺灣,希望學校老師能協助他接受現實,仍是個孩子的小光流著淚說,為什麼他一直被丟來丟去,一直要被拋棄,之前拋棄一次,現在又要再一次。輔導教師無言以對,能做的竟也只是陪伴與傾聽,就這麼陪著他慢慢長出自己的力量與勇氣去承接這一切的不可抗力。國二時,因外婆無力再負荷照顧之責,小光的媽媽決意將他轉學到南部有球隊且可住宿的學校。輔導教師找了機會和輔導主任去探望他,小光驚喜又感傷的眼神,清晰地令人難忘。 小光在畢業後回來過,笑著對輔導教師說,他可以回日本了,輔導老師能感受到他的五味雜陳,給予他鼓勵與祝福,相信這段成長旅程的意義,將隨著時間流轉在彼此生命的某一刻了然於心。 |
|
|